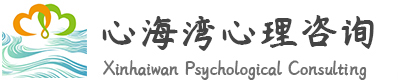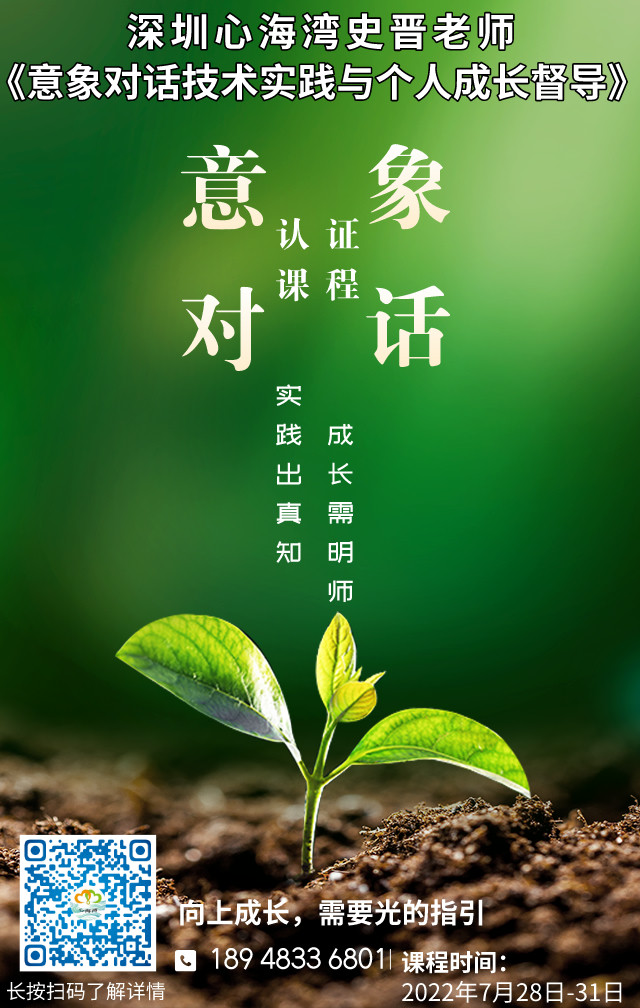转化的秘密——什么是心理的转化(一)
大家晚上好!首先感谢在座的每一位老师报名参加此次课程,你们的参与给了我心理上一个特别大的支持。同时我也要感谢咱们主办方——新疆乾德意象对话研究中心的各位老师,是你们搭建的这个平台,才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转化的三堂心理学课程。
当时在设计这个课程时,命名为《转化的秘密》,其中涉及到的是和心理转化有关的内容。在意象对话的心理学中,很多时候都在谈论心理上的转化。当然不只是意象对话,几乎所有深度心理学都会谈到转化这样一个主题,甚至在某些时候,转化本身是意象对话以及其他深度心理学工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我个人很想借由这三堂课围绕转化这一主题,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经验、一些探索以及发现。当然,这也意味着我讲的东西不可能涵盖关于转化这一主题的全部内涵,更不一定就所谓的标准答案。因为在这个主题下,我们会发现有谈也谈不完的话题,有永远都挖掘不完的内心当中的宝藏。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个人的分享,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出大家对“转化”的更多地宝贵地体验和发现。
心理的转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心理学家荣格所提出来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荣格本身对于我们中国古代的道家文化特别热衷,所以当我们谈论转化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说荣格恰恰是在我们中国人的道家哲学里悟出了心理世界的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所以作为中国人,其实我们对这个理念本身并不陌生。
那么什么是心理的转化呢?
荣格是这样来描述的:迄今为止那些尚未被意识到的心理内容进入到了意识当中。在这儿,我想请大家注意“迄今为止”这个说法。其恰恰是在强调,当转化发生的时候,哪怕是这一过程已然开始了,却依然是意识始料未及的。这意味着转化的发生是自我和意识没办法预计的。谁也没有办法在转化到来前对其有什么构想,这一切都是没办法预见的。或许有些时候我们能够借助以往的经验或此刻的直觉,从一些现象或者体验当中捕捉到转化的征兆,但往往也仅限于此了。
因而,当一些无意识的内容在意识浑然未觉的状态下,就骤然地进入到了意识当中,势必会给自我意识带来不小的冲击。而且,这样的心理上的冲击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或是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从而也令自我在转化到来时,进入到了诸如摇摆、震荡、不稳定,甚至是崩溃的状态当中。
所以荣格认为,转化会令人暂时性的失去自我,甚至会让人主观上感受到暂时性地失了神、失去了灵魂的主心骨。当无意识的冲击过大的时候,人会由此进入一种恍惚的、溃散感中,从而部分地丧失掉了自我的功能。
所以,当转化到来的时候,并不是一件令我们感到很美妙的事情,也并不会令自我感到舒适、豁然开朗,或者叫做获得了很大的、不一般的领悟啊等等,这些都是妄想,并不是主观上真实的体验。
如前所说,转化开始的时候,人的内心是被突然闯进来的无意识冲撞到的。这就好比在现实生活里我们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猝不及防的事儿,或者当自我经历一些无常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半天都回不过神来。这才是转化到来时最开始会有的样子。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所谓的无意识的内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其实都是被压抑的心理内容,都是或多或少我们在自我意识当中,不愿意去承认,不愿意去接受,不想去面对的内容。对待这些内容,我们甚至竟不想它存在于内心之中,不想它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平日里,这些内容经被我们用厚厚的防御机制压抑在心底里,也或是从我们有意识的主体人格当中分裂了出去。
所以当这些内容重新回来的时候,当这些内容涌现的时候,它很可能给我们原有的、稳定的自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些内容有可能从外边来,以外部刺激的方式作用在自我身上,也有可能打内部来,从内心中涌现。
大家肯定都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当我们做了一个梦,你从梦里突然醒过来之后,好像你的情绪一段时间都没办法平复下来,甚至可能这一天,这一周你都在反复的被这个梦所牵扯和困扰,你甚至可能会觉得,不要让我再想到这个梦了,但是有些时候,好像我们的注意力就会不住地落回到这个梦上来。我会纳闷,我怎么会做这么一个梦?怎么会梦到梦里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怎么会是梦里边儿那样的人?怎么会梦到那样的形象?这一过程无疑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冲击。
回到意象对话中,我们往往会在看意象时,也带出类似这样的体验。当一个意象在我们心里浮现出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在毫无准备和预期的情况下,引发了某种令自我备受冲击,甚至令人感到崩溃的情绪体验。
那么,接下来,转化的关键过程便由此开始了。在那迄今为止,都令人难以接受和承认的无意识内容不期而至,在心理上的冲击乃至崩溃过后,迎来的则是不得不去接受的“现实”。进而,就像我们在意象对话的过程中总是能遇见的那样,随着更为主动地一次次去面对,情绪获得宣泄,自我得到抱持——这都促成了“接纳”——这一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时刻的到来。
当然,这并非如描述的那般理想化。相反,在转化的整个过程中,随着情绪能量一波波地在心底里泛起,自我往往也会在一次次的冲击和崩溃中饱受洗礼。而说到接纳,则是转化的关键所在。
在转化之中,所谓“转”,指的是变化的发生。我们可以直观地将其理解成一种改变,一个跟以往不同的体验或是事件,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或是心中,从而进入到了我们的人格当中。
而接下来的关键则在“化”上。“化”的过程中,不仅有改变,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接纳”。所以你会发现,转化没那么快,转化不会一下子在短时间内发生,恰是因为那个猝不及防的改变,可能在短时间内,冲击到我们了,但是我们需要一个或长或相当长的时间在我们的内心去学会认识它、接受它,进而尝试着抱持它,并最终接纳它的过程。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某位成长中的心理咨询师在心里看到了一个通体都冒着黑气的黑巫婆的形象。很明显,这是一个看起来就让人觉得不舒服,甚至令人害怕、排斥,不愿意去面对和承认的意象。当时她自己都会很惊讶地说我怎么会看到这么一个意象?当然,就在那些颇为扰动的情绪在心里“开锅”时,我们便知道一个和转化有关的契机到来了。
正如我们能够猜到的那样,面对和接受这一意象的过程并不轻松。而十分常见的一种情况是,当身处转化当中的被带领者(的自我)难以忍受无意识所带来的冲击感时,往往会将“问题”向外进行投射,以求缓解自我的心理压力。她可能会说“都怪史晋带我看意象,都怪史晋让我看到了一个黑巫婆的形象”……
大家在未来的成长和咨询工作中也可以留意一下,当某些时候内心所体验的冲击感太强烈了,来访者或多或少会有一个心理的投射出来,比如投射到咨询师身上,也可能投射到周围的人身上,甚至投射向意象对话本身。比如,有的来访者会说这个咨询师有问题,这个咨询师没带好,或者说成是意象对话有问题,这个方法有问题,不然怎么会让我看到这个东西。而实际上这是他自身的人格在这种转化到来的时候,出现了极大的晃动和不稳定感所造成的。进而,随着他的内心、自我,一点儿一点儿地在接受那个部分,“化”的过程、接纳的过程,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一点发生。
就像我举的这个例子当中,我带的那一位伙伴,过了几个月,他就说好像现在没那么大影响了,我能在意象里看到它了,我能在意象里看那个黑巫婆儿了,这个转化就完成了。当然,这时候她也不再认为带领者有问题或是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存在问题了。
这一看似颇有成效的转化,并非就是所谓“大团圆”的结局。因为正如荣格所说:“永远不要把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描绘成为一个结果”。一次转化的结束,往往预示着新的转化的开始。
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特别有意思,就这个意象本身,在我和这位当事人的讨论当中,她提了一个问题:“奇怪的是,为什么我挺讨厌这个黑巫婆的意象,但是一连几个月,我怎么总是看见这个意象,甚至还在梦里梦到过她,你说这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还有什么我没看清楚的?”
当她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也着实让我在心理上产生了一个不小的扰动,一个突然撞进来的无意识内容也同时引发了我特别多的思考。我感到心里有一个深深的安感,但是我还是和她说出了我的想法。为什么一个令我们唯恐避之不及,甚至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接受它的存在的意象,却总是出现在你的想象当中,甚至出现在梦里?其实很简单,是因为在心里你想它了。确切地说,在你心里有一个人格深深地挂念着这个(黑巫婆)意象。
当我把联想到的这些和她讲了以后,如同在心里又一次掀开一个尘封已久的盖子,一大簇无意识的感受,便从这儿开始涌现。一时间,她没有办法接受我的这个说法,更不能相信原来在心里她其实是盼望见到这个“黑巫婆”的……
随着新一轮冲击的到来,她指责我说,这种分析是不负责任的,完全是是野蛮分析。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回过头来开始慢慢尝试着接受这一说法。她解释说,的确有可能像我说的那样,至少她内在的一部分人格真的是向往它(黑巫婆)的。为什么呢?因为她通过心理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意象中的“黑巫婆”其实像征了她童年生活当中的那个坏客体,是心里上的“坏妈妈”的化身。
虽然在和坏妈妈的关系中,不仅会令人感到害怕,甚至还会遭受种种创伤。这些体验无疑都是真实的。然而,我们需要考虑到的另一个因素是,在婴幼儿的心里,对母亲充满着向往和渴望。这样一来,又惧怕又依恋——这二者的矛盾看似就能解释得通了。
或许从她的这种解释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些心理防御机制的影子,诸如理智化,等等。但也或多或少的确有着接纳的意味。起码她的自我意识给了那个“期盼黑巫婆意象”的这一说法一条生路,她在试着去接受甚至忍受这一说法的过程中,转化就再次发生了。
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一个转化才刚刚落幕,新的议题便接踵而至。
这一次在她心里又经历了什么呢?在生活当中,她一下子看明白一件事情——黑巫婆的意象,或许在某个层面上,象征了内心里的那个坏客体、坏妈妈,但是说到底这其实是她自己。她甚至发现有的时候,对周围的人,尤其是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时,她简直像极了一个“黑巫婆”。
可想而知,这一下子的冲击感无疑更强烈了。当她将一个被客体化的心理意象,一个投射在母亲身上的意象收了回来,而正是这个收回投射的心理动作带来了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扰动。此刻,她要面对的是自己人格当中那个“黑巫婆”的部分了。
每一次转化的发生和完成,都是一个阶段性的成长任务、目标的达成,也正如荣格所说,原本那些被我们排斥在意识生活之外的潜意识当中的部分,它们如今融入到了我们的主体人格当中,并和我们原有的自我,在激烈地冲突和对抗之后,发生了创新性的融合。转化永远不是一个结果,它更像是一个目标——在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的人格趋于不断地完整。
与此同时,荣格也用了一句很坦诚的话来描述说,“我们可以将每一次阶段性转化的完成,都视作是一次象征性的,经历了旧有人格的死亡,又走向新生的过程”。
围绕转化的过程,另一件值得留意的事情是,在我们的人格深处,原本那些潜藏在暗影当中,不被接纳甚至是令我们唯恐避之不及的潜意识部分,其中往往蕴藏着丰富的人生资源。
很难令人想通的是,一个黑巫婆的意象,其中所携带的那些心理能量无外乎都是跟死亡、阴影、恐惧、悲伤或绝望等等有关的东西。它有什么资源性可讲呢?难道有谁会盼望这些能量来到我的身上,或者成为自身人格的一部分吗?

为啥呢?因为在心里我都见识过“黑巫婆”了,和这个意象打交道的日子里,自己早就被锻炼出来了。她并不是在心里战胜和打败了那个黑巫婆,而是看到、理解和接纳它的存在。这样一来,这个意象(及其所携带的内涵),也都成为了她的主体人格的某个部分,甚至是富含资源的部分。所以打这以后,当来访者呈现那些但凡是和悲伤、抑郁,乃至死亡等有关主题时,她不仅能够给予陪伴和抱持,更能和来访敞开去谈论那些感受。
转化的秘密——转化发生的三要素(二)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的,是关于转化发生的三个重要的因素。在我的个人成长以及意象对话的咨询工作当中,发现如果我们能在这些要素上有所留意,对转化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转化发生的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呢?是对想象力的训练。心理的转化,从意象对话的角度来看,是借由意象本身来完成的。而意象又是怎么来的呢?是我们通过想象在内心世界里面看到的。这就意味着,如果让转化更好地发生,想象力是这一过程当中不可或缺的。
你想让人格发生改变,甚至想要人生都发生一些变化,没有想象力肯定是不行的。但偏偏对于成年人来说,我听到的关于想象力的描述里最多的两句话就是“我难以想象”和“我不敢想象”——我不敢想象,有些好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难以想象,自己不再是现在的样子……很多时候,作为成年人,我们学会了用厚厚的防御机制,将内心中那个敏感且受伤的部分一层一层地缠裹了起来。看似我们都期待能有所改变,实则我们都很害怕改变,甚至拒绝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只图一个明天和今天能是一样的,只图一个同样的事,在我的生活里反复发生就好了。
但问题是,假如我们不敢想、不能想,总是置身在一个想象力匮乏的沙漠当中,你又怎么能让转化得以发生?你连想都不敢想,改变怎么会到来呢?所以我经常会半开玩笑地跟我的同行们说,意象对话的工作,就像是在做心理世界关于想象力的扶贫工作。对于成年人来说,就是要将那片贫瘠的想象力的土地,让它重新焕发起原有的丰饶。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意象对话不仅仅是用在心理咨询和个人成长当中的,而是要用在生活里。用意象去看事物、看心境、看关系,再回观自己,多去链接诗词、艺术、音乐和文学,当然还有梦境,借由这些心理世界中丰富的意象资源,去唤醒我们的意象思维。
而没事的时候,哪怕你在上班通勤的路上,或是高铁、飞机上,把手机、短视频和游戏丢一丢,读一本有趣的书,带着自己做做意象,再眯上一会儿做个梦……
当我们的想象力够丰富的时候,你就像是抓到了许许多多的,跟转化有关的可能性。不要说我不敢想象,不要说我不能想象,要让自己闭上眼睛回到自己的内心,带着感受,勇敢地说出那句“我在想像当中看到了”。
跟转化有关的第二个要素是深刻而生动的体验。当一个意象被看到。尽可能带着感受试着深入地体验下去。在荣格看来,在我们内心里潜伏多年的潜在人格,乃至每一个意象都有一个夙愿——这个夙愿就叫做,每个意象都想真实而深刻地活一次。试想一下,如果你是那些活在心底里的居民,却看到每天占据着这具肉身的人活得如此平淡平庸,你会是什么感受?你一定会有一种深深的不甘心。甚至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那个叫做“自我”的家伙,居然为了所谓的安稳日子而甘愿把生命活得如此卑微猥琐。
一个我们在内心中看到的真实的意象,比起自我来说,它们反而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刻。甚至相比之下,意象才有资格被称为“活着”的存在。无论是一位英姿飒爽的“侠客”,还是楚楚可怜的“少女”,亦或是张牙舞爪的“妖怪”——在意象的内心世界里,哪怕是一花一树,一只猫咪都会是如此真实而生动。因而,我们要向意象去认同,虔诚地恳请它们带自我去往那个久已被遗忘的心底里,去寻访关于生命的真实的存在,找回对万物的深情。而所有那些在体验中足以打动心灵的时刻,都会推动转化的发生。
转化的第三个要素,是忘我。前面我们讲到,当转化到来的时候,人会进入那种暂时性失去自我甚至失魂的心理状态当中。我们都知道那种状态确实不好受,但如果自我此时不想交出对意识心灵的控制权,转化便永远都无法发生。
说起来,自我的需求是什么呢?作为经验(旧有人生)的集合体,自我就是要寻求一个稳定感。所以当人活在意识自我当中的时候,生命被自我所支配,他是没有办法预见、无法想象生命的未来以及诸多可能性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自我貌似能够有所期待的无外乎只是能够令其感到满足、安稳并完全得以掌控的一切。
这就好像我们在引导看意象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的诸多情形那样。例如,被引导者会睡着,或是看不见、看不清意象,当然更常见的是看到意象却没有什么情绪和感觉……实际上,诸如此类情况,大多是由于自我不愿放手对意识的把控,甚至害怕意象的出现,令某些难以应付的、突如其来的潜意识内容猛然闯入进来,从而竖起的防御壁垒。
因此,在引导进入意象时,我经常会暗示对方说,“接下来不用刻意地去想象什么,我们只需要将一切交给想象力本身,等在那儿看着一切自然而然地在心里浮现出来就好……”
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在做意象时,我们常会先带领体验者做一个放松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引导身体的放松,进而带动自我意识放下心理上的戒备。所以在带领体验者做身体放松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来引导——随着身体的放松,我们也让自我意识慢慢地松下来。我们也让自己心里边可能有一些紧张和焦虑的心慢慢地松下来,一点儿一点儿地松下来,松一松当下我们身上的劲儿,也松一松我们在心里边儿的这股劲儿。
关于转化中的想象力、投入和忘我,我想多谈一个我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做一个额外的补充。这三者以及面对、陪伴和抱持、接纳等等转化中的重要因素,其实是可以通过某种日常生活中就有的方式得以训练和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做梦。你想让自己的转化能力变的很好,做梦去吧!
首先,一些做深度心理分析的治疗师,他们会认为做梦这件事本身就是转化的发生。这恰恰是因为在梦中,每每就包含了我们所提及的三种要素。
其一是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形容想象力之丰富,会常用一个词来描绘,就叫做“天马行空”。开个玩笑说,这匹马打哪里来呢?当然是“以梦为马”。在梦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梦的想象力,简直无比丰富。
所有的事儿都可以在梦里那么直接地发生。比如你可以从悬崖上跳下去;你可以凭着自己的能耐飞起来。你可以穿梭时空,也能死而复生。当然还有一些很疯狂的事儿,或者是一些令人感到害羞脸红的事,它们都可以发生在梦里……所以梦其实本身是对缺乏想象力的现实生活的一种扩充。所以如果你能学会和梦去打交道,你的想象力就在不断地开发和得到锻炼。这无疑会给转化的工作提供许许多多的思路。
于此同时,第二个转化的因素——生动地投入其中,也包含在做梦这件事上了。在梦里你所经历的所有的事儿,都是感觉无比的生动和深刻的。甚至在很多时候,现实里决然不可能发生的事,在梦里也能真实而深刻地去经历它。
我自己曾做过这样的梦,在梦中我变成了一个孕妇,经历了整个生产的过程。而就在孩子刚刚降生不久,就有人将我们“母子”强行分开。可想而知,当时在梦里我哭得撕心裂肺。那种经历在现实中,对我而言,绝无发生的可能。但梦里却是那样的真切。以至于醒来后,我半天都恍恍惚惚地回不过神来。
最后,第三个要素,你会发现,对于妄图掌控一切的自我,梦可是丝毫不会有所顾及。直白地讲,自我没办法主导在这个梦究中会发生和经历什么。你仅仅只是被推着走进或者被放到了某一个梦中,而这个梦境的缔造者则另有其人。
当然,这也意味着,哪怕再有掌控感的自我,在梦中也做不了什么。自我想让这一切都如现实一般通过我的努力通过我的执着,通过我不惜任何代价的牺牲来去获得满足,在梦里却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在梦里我们慢慢就学会了有些事情不用你管。有些事不用非得按照你的意志让他如你愿的那样发生。如此一来我们就把一件事儿该怎么推进下去,或是把一个故事该怎么讲下去交给了故事本身,而自我呢?学会看着这一切发生,看清发生和经历的过程,带着感受,带着对心灵和生命的敬畏之心,看着就好,看见就好。
我补充这一段,就想跟大家说如果有缘咱们从今天开始就让自己去留意自己的梦。你也不要问我说该怎么跟梦打交道,该怎么解这个梦,然后记不住梦怎么办,没有梦怎么办。那个心诚则灵,如果你在心里边儿真的发愿你想通过梦,去让你的人生发生一些变化,通过梦让你的人格经历一些转变的话,一定就会有梦。慢慢学着跟Ta打交道就好了。
转化的秘密——改变意象与转化的关系(三)
接下来咱们就进入这堂课的第三个板块,讲一讲意象对话中的改变。通常,我们在做意象对话的时候,在自我意识的参与甚至主导下,对意象所做的改变或在想象中实施的带有主观意志的修改,这些并不是心理上的转化。虽然改变有的时候,可能会促进转化的发生,但它并不是转化本身。
虽然其本身并不是转化,但意象对话中的“改变”有没有意义,却有着十分重要的心理意义。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当一个人遭遇到现实或是内心当中的某种心理上的冲击时,转化是否能够发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人是否拥有一个足以能够承受痛苦,忍耐所有这一切的自我。
相反,若是自我缺少相应的张力和耐受度,同样的冲击只会造成心理上的创伤。而在过往历程中,那些反复袭来的伤痛感,往往会令人深陷绝望和无能、无力以及无措当中。相应的,我们则会在心里看到诸如那些孤苦无助的、置身绝境的,以及毫无希望感的心理意象。
在意象对话当中,围绕此类意象,我们有意识地主动进行的“改变”工作,便显现出了其建设性意义所在。通过这种积极的“变”,足以向来访者传递一个关键的理念:假如这个世界总是令人感到受伤,你至少可以学会照顾好你自己,疼惜你自己,或者保护好你自己。假如你习惯了敞着伤口,等待一个永远不会来到你身边的人为你疗伤,那么至少你可以自己为自己去疗伤;假如你的人生总是充满了孤独,但是你又等不来那份你心中期待的陪伴,至少你可以陪伴你自己的孤独……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我在意象里看到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破破烂烂,屋里边的很多东西都是用手一摸,积了厚厚的灰了。窗子上的玻璃,也都从来没人擦过,顶蓬上结满了蜘蛛网……相信大家都能看得出来,这栋房子的状态,就是看意象的人的心境,是那种蒙了灰一般的抑郁的心态。
这种灰暗的心情,或许长期缺少他人的关注和爱所造成的。由此一来,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便逐渐忽视了对自身的照料。就像是一个婴儿,假如妈妈不及时过来哺育我,又疏于对我的照顾,那么我又怎么会哺育和照顾我自己呢?客体从来不为我这样的事,我自然也学不会。
但是这时,我们可以在想象中自己把这栋房子打扫一下。擦擦桌子、扫扫地,再把窗帘打开……随着意象里的这样一番“改变”,我的心情似乎也变得好了起来——就像阳光照进了内心,感觉敞亮多了。
而这就是“改变”的意义所在。通过这种积极主动地“变”,我们获得了一种理念——假如这个人你没等来,不妨你可以试试,为你自己做这件事儿。改变所带来的积极的心理体验,也令人的自我获得了信心,从而增进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养成——如果我想达成一个目的,不用非要从谁那里得到什么,我可以试着为自己做做看。
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作为“转化”发生的准备工作,“改变”可以被当作是对自我所做的锻炼——通过这一心理建设的过程,使自我获得相应的信心与张力,从而迎接在心理探索和成长路上不期而遇的转化。
所以在这儿,我想和大家着重谈一谈的是,“改变”可以用,但不要经常用,而且更要去觉察的是,通过改变意象而带来的那种心理上的安慰,甚至是无所不能的满足感。尤其是在面对那些给我们带来诸多负面情绪、困扰,乃至心理上的冲击感的意象(议题)时,若是每每都只是通过改变使其得以缓解,或是获得安抚甚至有所好转时,真正的转化便不会发生了。
因为每每当我使用改变的时候,我能很快“解决”掉来访者心理世界当中的困扰和问题。甚至我也收获了来自来访者的那种崇拜、仰慕、掌声。但是这只会让我越发自恋,令自我进入更加膨胀的状态。但对来访者而言,问题并没有真的得到解决,而仅仅只是“消失”不见了。当然,这里说的消失,其实是压抑到了更为深层的潜意识当中。因为原本浮现上来的,因为想要解决和改变,却没有得到接纳,于是便值得掉头回去,再次深埋心底。如此一来,唯一得到满足的,只有自我而已,人格并未真正成长起来。
所以要擅长使用改变,但是不要迷恋改变带给我们的满足感。每一次的改变你我都要知道的是,仅仅只是为接下来要面对所做一个准备。
举例来说,我看到在意象当中,有一个被冰冻起来的少女的形象。随着这一意象的呈现,来访者也感到心里充满了冰冷和绝望。这时我该怎么办呢?于是,我跟来访者说请你在想像当中陪伴她,温暖她。一个被封在冰中的少女,她缺少的是那种温暖感。甚至我可以跟她说你想象你在她旁边点起一团篝火。随着这个篝火的燃烧冰在融化……果不其然,来访者在想象中这个冰真的一点点就化成了水,与此同时来访者也是热泪盈眶。这个时候我还赋予了她一个解释,我说多年的坚冰在融化的时候就会变成温暖的、充满热情的泪水。继而,这个意象中的少女从冰里复活了。
来访者会说太好了,我内在的一个女性的子人格从此得到了新生。但那其实不是的。那是一种我们伪造的,用来满足自恋的,一场自欺欺人的梦幻。不然为什么多年以后,这个来访者又回到咨询室里,她困惑说同样的问题又在现实里发生了,同样的事我怎么又是这样经历了?甚至她再一看意象,这个几年前被解救出来的“女孩”,又被冻回到冰里面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本该去面对一下,当你看到一个少女被冻在厚厚的冰层下面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受?这可能才是我们真正忽视掉的东西,这时的内心体验,才带来转化的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留意一下,改变是为了转化的发生而做的一个准备,是为了让来访者获得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就叫做不要对你的内心感到绝望,没有人为你做,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关心你的时候,你可以为你自己做点什么,可以爱你自己,可以关注和表达你自己。但是,我们获得了这种希望感和力量感的时候,你不是要用它去满足自我的自恋,而是要用它成为你在面对的时候内心当中的勇气。
咨询师尤其要对“改变”保持觉察。因为在改变发生的背后,往往有着某种尚未被意识到的意志。以刚刚这个例子来说,很可能在咨询中,咨询师并没有引导来访者说,想象中在被冰冻的少女身边点起篝火。可这时来访者自己却表达说,“我陪着她(冰冻的少女意象)的时候冰也开始一点点地在融化。”看起来这像是意象当中自然而然地发生,但似乎这中间的转化发生得太快了。可能来访者想要急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也或是她其实不愿面对转化带来的痛苦体验。甚至来访者带着某种对咨询师的“迎合”,盼望咨询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神奇效果……
相反,就这个意象来说,如果是真正的转化,来访者在做面对时,她不会感觉到那股暖流很快地生起,反而会体验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冰冷感。她会感觉到说怎么在三伏天,她竟然浑身都在打哆嗦——我怎么会那么冷!我承受不了这种感觉,我觉得自己特别绝望,我觉得整个身体都是僵的,都是木的、都是麻的,连我流出的眼泪都是凉的……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她才是真的和这个意象是在一起的,她在体验、在面对,而后才有可能真的迎来心理上的转化。
有的时候,在咨询当中,或是在成长的团体里面,通过某些话题的引发,参与的伙伴往往体会到各种各样的身体上的不适。比如我今天听了一天的课,我觉得我的头疼、后背疼、肩膀疼,或者肋骨疼、小腹疼,也可能在小组里有谁谈到了一个感受,然后我就觉得浑身都变得不自在,反胃、打嗝、胀气,一阵阵打哆嗦……我能理解这个时候感受上真的十分难挨住,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恰恰是转化的契机。
而且令转化发生的关键,恰恰是在此时带着觉察去耐受这一切。这个时候可以带着感受去看看意象,或是陪一陪我们此时的身体和情绪。当然,这里要说的是,耐受是有觉察的,即我知道我在承受内心乃至身体上的不适和痛苦。相反,如果这时没有带着觉察,仅仅只是很被动地忍着、挨着,反而容易被绝望、无助和无力带走。因此,在很难保持觉察的情况下,有觉察地不去忍受——比如,主动带出、离开,或是不再看、不体验,有觉察地让自己回一回神,回到意识中来,有时也有助于转化的发生。
转化的秘密——彩蛋环节(四)
使用意象对话时,有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在“改变”中,引发或是促进转化的发生。而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意象对话的关键理念。说起来呢,很多的心理学流派、方法和技术中,都会使用到意象。比如,释梦、自由联想和积极想象技术。当然,还有一些心理学的方法,他们会直接在意象层面上做改变,在心里通过想象,植入积极意象或是修改消极意象。而我们都知道,这种方法其背后是对心理内容、心理问题的不接纳。如此改变,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还会引发无意识的反噬。
虽然都用意象,但在理念上,意象对话和这些传统的心理学流派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在以往的心理学,经典的精神分析,心学理动力学,后来的精神分析,包括荣格的心理学等等,其主旨都是在强化自我。甚至从弗洛伊德开始,精神分析就被叫做“自我心理学”。其认为自我是无比重要的,自我是工作的目标,以及强化自我的功能性就是心理分析的目的和意义。因为正如弗洛伊德在描绘“三个我”时所说,“自我是一位艰难的‘驭马者’,他一手要牵拉着放荡不羁的本我,一手还要紧紧拽住桀骜不驯的超我。”可见只有自我变得强大了,他才能立足于现实,并将这三个我统合到一起。
举例来说,在精神分析的视角下,通过分析的工作,那些原本深埋在潜意识中的动力和内容被成功地意识化了。一个来访者通过治疗,慢慢锻炼出来了更高阶的,更成熟型的心理防御机制,这个令自我成长的目标就达到了。比如,一个人原来总是投射和抱怨,把各种问题都推向他人和命运。后来,他慢慢学会了合理化,这就是他在防御机制上的进步和升级。然后慢慢地他又学会了幽默地表达,甚至能够调侃自己的心理问题了,当然他比以前更有对磨难的忍耐能力,不再轻易地就总是放弃——诸如此类,那么我们就说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升级了。他就变得比以前更健康了,自我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有了更好的适应性,症状也基本消退了。
实际上,这可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接纳,甚至不无偏颇地说,这只是对潜意识的压抑的手段更为高明了。同样,我们再看荣格的心理学。荣格因为自我应该跟潜意识达成一个和解,去主动认识那些内心深处的、古老的、原始的潜意识智慧。相比强化自我的功能,荣格会说自我是一个情结。但与此同时,荣格却又不断强调“自性”的重要性,他甚至将自性摆在了“生命的源头”、“一切的目的和意义”、“原型之原型”这样重要的心理位置之上。当然,如果我们知道所谓自性,其实就是那颗萌发并长成自我的“种子”,便会就此看到,这无疑是在强调,自我在心理世界当中,其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且根深蒂固的。
但是这个过程又会导向一个问题,那就自我的膨胀。对自我来说,其获得了一种心理经验——潜意识不一定要压抑它,而是通过某些方法将其变废为宝,转化成为自我的财富和资源,让心理世界的一切都能为“我”所用。在这个过程中,人格未必真的获得了成长,相反在全能自恋的助长下,自我中心被不断强化。漫谈一句,这正是西方的哲学、心理学乃至文化走向死角的一个关键原因。而自我膨胀的实质乃是一场虚幻的梦境。荣格觉察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指出自我中心的危险在于,无意识终会发起最后的反攻,令自我意识在膨胀的至高点上,马失前蹄,一落千丈。
言归正传,意象对话的理念将这个问题巧妙地化解了。在这里,自我也被视为心理世界中的一个意象,与其他所有象无异。实际上,在意象对话初级班的课程里,就在试图将这一理念传递给大家。这就是“看镜子”的意象。不信你在心里照照镜子就会发现,我们以为真实存在的那个自我,其实也只是一个意象而已。那些“我”看到的意象并不是由我所造(想象出来),更不是“我的意象”或“我的子人格”。包括“我”这个意象在内,我们都是“象由心造”。当然,我们常常所说的所谓“我的心”,其实也是不对的。作为心灵所描画下的一个象,“我”一直都身在心内。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把自己当真了,以为其他的一切都只是我看到的象,只有我才是真实的。
我也是一个意象——带着这样的理念,我们便不再是看意象的人,更不是意象的创造者和拥有者,由此我们设身处地来到了想象的世界中,以一个意象的身份,同其他所见之象结成了关联。这时,即便是在意象中做改变,那么这种改变也已然不再是修改那些不好的意象,而是用生命去联结、对话和影响生命。
如果具体到意象对话的过程当中,引导者可以加上这样一句引导语——请想象你自己亲身走进了这个意象的世界里,并且来到了(某个)意象的跟前。这个过程不要太快,而是先要去找找感受,让这个想象中的世界(环境)变得更加具象和生动,仿佛你此时正身临其境……你可以试着在想象中和意象交流对话;可以陪伴在ta的旁边;如果你想为这个意象做点什么,不要想象你已经做到了,而是要真的动手去这么做……
举个例子,某位来访者在心里看到一只受伤的小狗的意象。然后这个时候她说她要给这只狗疗伤。于是,想象说在意象中来了一位兽医,或是想象来了一辆车把狗带到了医院。很快这只狗就被治好了、康复了。然后当看到狗在意象里活蹦乱跳的特别开心,于是她也从难过、绝望中变得快乐起来。到这儿,各位一定知道,这不是转化,而是自欺欺人。
如果是我们上边讲到的理念来做,我会引导看意象的人说,请你想象你自己来到了这个意象的世界里,去到了这只受伤的小狗的身旁。你先别着急做什么,你就这么看看它。这时候被引导的人说到,她觉得这只狗太可怜了,她希望能令它好起来。至少是可以先为这只狗治治伤。
于是,我引导她说,请你在想象当中亲自来到这只小狗的身旁,然后你先看看狗受伤的伤势情况。同时,你体会体会你当下的内心感受。这时,在强烈的体验当中,这位来访者说到,看到意象中狗的伤势时,她根本就不敢去碰,因为太惨烈了,太令人感到恶心了。甚至她都在想,受了这么重的伤,干脆死了算了,死了就解脱了。你看,显而易见的是,站在外面看意象,和走进意象当中去经历所发生的这一切,效果截然不同。而且,我们都知道,这种在面对真相时所带来的心理上的真实的冲击,才是转化的先兆。
因此,如果在心里真的想要救这只狗,你就在想象中,带着内心的真实体验,一点儿一点儿地帮它清理伤口,再一步一步地把它包扎好。在这个过程中,你因为对惨烈、无力、恶心和厌弃等等这些感受的耐受,又在一次次从心中升起的放弃感里逐渐找回了对生命的笃信,从而使得心理上的转化在对意象的“改变”中发生了。
再举个例子。有位来访者在心里看到了一个很孤单的小男孩的意象。这个孩子身处一个旷野无人的荒原中,面对黄昏呆坐在那里。乍一体验,这个感觉让人特别无望,一切都显得毫无生机。这时,来访者想象说,我从子人格中调来了另一个小孩儿的意象,我想象他们在一起玩儿,于是那个孤独的男孩儿就有了陪伴,也就开心了。这并不是转化,反而是对孤独的不接纳。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很简单,你想象自己走进了这个黄昏的、旷野无人的环境里。你可以摸摸这个世界的土地,抓起一把沙砾,感受一下迎面吹来的风,看看四下无人带来的感受。这时来访者说到,在这个环境里,会令他感到无比的压抑、憋闷,同时也会有种隐隐的恐慌感。这令他想要赶紧离开,一刻也不想多呆。接下来,我引导来访者说,请他带着这样的体验,去到那个男孩儿的身边。于是在想象中,他走到男孩儿那里,在他旁边坐了下来。而这时,来访者的情绪一下便涌了出来。他说在这之前,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孤独的,也不曾体会过绝望。直到自己走进意象,看到了、亲身经历到了那个男孩儿眼中的一切……那么,此时还需要对意象做什么改变吗?其实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们只需呆在意象里,陪着那个男孩儿,也陪一陪身在这样的绝境中,感到孤独绝望的自己就可以了。
转化的秘密——转化和原型的关系(五)
这次要和大家聊一聊的是,心理的转化和原型之间的关系。
首先,咱们说说什么是原型。按荣格定义说,原型是集体潜意识的基本结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那些每个人、人格当中皆有的、人与人共同的人生、生命主题。例如,我们都是由母亲怀胎十月所生,又都离不开母亲的哺喂和养育,因此在我们心中便都有一个“母亲”的原型。每个民族都有英雄的传说,因此“英雄”也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原型。除此之外,那些人所共有的生命主题,例如出生、爱情、冒险、牺牲、欲望、死亡等等都是作为人格的基本结构而存在的原型。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原型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我们内心的心理功能和心理品质。例如,阿尼玛(女性原型)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情感、感受的心理功能;阿尼姆斯(男性原型)则是人的理智、理性和逻辑思维的功能。同样,英雄原型在我们心里,是勇敢、正直的心理品质的代言人;而魔鬼原型,则是欲望、诱惑和堕落的体现。
其实早在心理学出现之前,人们也和原型打交道。只不过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原型”这样的概念。那时的人们将其称之为神明或是命运。比如,当一个西方的古人坠入爱河之时,他可能不会说自己心里的“爱情”的心理功能被启动了,而是会用某种颇为浪漫的说法——我的心被丘比特(爱神)的箭给射中了。当然,更为熟悉的故事里,我们中国人则更为含蓄,也许会说,月老帮我牵了红线。
与此同时,无论作为心理功能抑或是人生的主题,原型还可以被看作是所有与此有关的心理现象的集合。每一个原型都是这样的一个口袋,在这个口袋里,装满了与此有关的所有的故事和心理现象。而所谓“所有”一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任何一个原型之内,故事的讲述都充满了各种可能——这些故事之间可能存在相互的关联,也可能会被随之带往截然相异的命运轨迹。还是以“爱情”为例,在这个口袋之中,装满了人世间的各种爱情故事——有我们期盼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有彼此总是擦肩而过、咫尺天涯;有动人的,就有令人惋惜的,有阴差阳错不期而遇的,还有历经考验眼看便可长厢厮守结果却阴阳相隔的……正是这些讲也讲不完的故事,为心理的转化铺设了无数的前路。
而说到集合、口袋,我们也可以将原型——或者确切地说,每一个原型都看作是一个容器,在这些容器之内也或容器之间,为心理能量在“转化”的过程当中提供了涵容与承载。
接下来,让我们讲一讲,转化和原型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概括地说,一切心理的转化,要么发生在某一原型之内,要么则发生在不同的原型之间。
仍然还是以“老巫婆”的意象来举例,起初在心里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令人感到无法面对,更难以接受。而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过和这个意象去打交道(面对、陪伴和对话),在耐受了种种情绪、痛苦乃至身心煎熬之后,随着一点点的接纳,转化也慢慢发生了。我从起初内心充满了对这一意象的恐惧,到后来居然会感到对“老巫婆”的几分怜悯,从对这个意象的拒斥,逐渐理解了是怎样令人不免哀叹的遭遇,令一个心理世界中的女人,成为了眼前这个满心怨恨的邪恶巫婆。
而且,在意象本身上,这一转化的体现则更为直观。当我们围绕这个意象对情绪和感受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抱持后,意象中原本的那个看起来给人感觉恶狠狠的“老巫婆”,慢慢变化成了一位有魔法的老婆婆的样子。在想象中,这位婆婆不仅能占卜,还会做一些解毒和治疗的药剂。而且,在对待“看意象的人”的态度上也有了明显的转变——从开始时的怨恨与迫害,到现在终于可以正常交谈了。甚至后期当我们在心理世界中有求于她时(请她帮忙照料一个受伤的流浪儿的意象),我们竟真的从她那里得到了暖心的帮助。
然后这个时候带着这个感受,我再看这个老巫婆的意象。这个老巫婆就变成了什么呢?这个老巫婆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没那么凶恶的一个婆婆的形象了。而且我发现这个婆婆,好像还有点儿本事,我看到她在意象里,好像她还会算命,她还会配一些药,这个药对人还有一些治愈的效果。你看这个婆婆怎么会发生了这么一个变化?其实这个转化就是在原型之内发生的转化。而这个原型是哪个原型?当然我们不一定非得要学习原型,我就在这儿给大家举例子,这个原型就是大地母亲原型。
大地母亲原型的故事里,包含了许许多多的好妈妈的故事。你看这个世间,有无数种好妈妈的样子,又滋养又包容,又有爱的那个样子。我们一举古今中外许许多多这种例子,你打开看好妈妈的新闻,你百度搜一下,好几十页。同时,这个世间,又绝对不缺少坏妈妈的样子。
坏妈妈的意象和坏妈妈的故事。在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咱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么一本血泪史。咱们在座的300位,每个人都可以翻一个坏妈妈的故事出来,抱歉,开个玩笑哈。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转化就是在大地母亲这个原型之内,从坏妈妈走向好妈妈,而且他们之间又不是毫无联系的。这个变成了一个好婆婆之后的老巫婆,她为什么会配一些能够治疗他人的疾病的药?是因为她的另一面,特别擅长给人带来创伤。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好玩的对立统一,疗愈和创伤,它们是一体两面的。
这也就是荣格经常会将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比作是什么?比作是受伤的疗愈者。就是因为我们都有受伤的经历,都有受伤的经验,所以我们才有疗愈他人创伤的能力。你看这就在原型之内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立统一的一种联系。一个给我带来伤害的,然后他的另一面其实是能带具有那种所谓的疗愈的功能,这就是在原型之内发生的转化。这个转化让我从创伤走向了疗愈。并且在我内心里,经由这个转化,我理解了创伤和疗愈其实是一体两面的。荣格经常说的一句话,叫“解药就在毒药之中,解药就在毒药的核心处”,荣格经常会讲这个话,因为他看到太极图的时候,他就会发现阴极走到顶点是一个向阳的转化,而阳极走到顶点是一个向阴极的转化。
就拿大地母亲这个原型举例子说的话,在咨询中,人们常常会说,自己的童年是缺爱、陪伴与关注的,因此在我心里多么渴望一个好的客体。假如我们看到一个妈妈竭尽所能地给了孩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陪伴。我猜这样的爱与照料,是很多人无比向往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来自妈妈的爱过于浓烈,乃至在婴儿期、童年期,甚至到了青春期妈妈的陪伴和关注依旧无所不在的话,一个人就不会觉得这是种美好的体验了。相反,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妈妈太过控制了,让人觉得在她的笼罩之下,有一种窒息感。这就是母爱中具有吞噬性的一面。
一个孩子在幼年时得到了很多的照料,被妈妈保护的太好了。但当他长大成人步入社会之后却感到了屡屡受挫,这是因为他从小便缺少对挫折的历炼。相反,一个在童年时没能得到足够关注的孩子,他虽然心理上是有缺失感的,但或许多了更多的自由,也从小便锻炼了独立解决问题和照顾自己的能力。
实际上,在每一个原型中,你都能看到这种一体两面的统一性。这就好像我们古代的道家哲学所描绘的那样,所有事物中的某一面走向极致、极端时,其相反的对立面效果便会就此呈现。
除此之外,另一种和原型有关的转化,是在原型之间完成的,也就是跨原型的转化。这就相当于将故事从某一个原型那里,带到了其他的原型之中。或者说,从某一种命运里去往了另一条命运的轨迹上。
比如说,我在意象里看到了路边上有一个被丢弃的、哇哇大哭的一个婴儿。这很可能是一个弃儿的意象,同时我们知道这个意象在心底里,关联着集体潜意识层面的弃儿原型。这时候,我就让自己一边去体会这个意象,抱持这一过程中我在身体层面感受到的冰冷感,以及内心不断涌出的强烈的恐惧和悲伤等情绪。与此同时,我也试着让自己尽可能地在这样的体验中耐受着,并且陪伴这意象中的这个小小的“弃儿”。一段时间之后,意象中的这个弃婴似乎慢慢安静了下来,我能看到他正睁大眼睛看着我,嘴里还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接下来,我在想象中将其抱在怀里,又用奶瓶给他喂了些奶喝。我看到这个原本是个弃婴的孩子,他好像不再饥饿,皮肤似乎也有些红润的色泽,甚至在我怀里他竟然咯咯地笑了起来……深圳心理咨询专家
这就是发生在原型之内的转化。如同硬币的两面,每一个原型都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因此,弃儿的对半就是宠儿。通过陪伴意象的过程,心理的转化将我们从被抛弃的命运中,转而带往了这种命运的相反面上——宠儿的体验在内心里就此涌现。
心理的世界由无数的故事交织而成,在另一种可能性中,弃儿的意象去往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轨迹。例如,体会弃儿的意象时,我在想象中看到,有一位骑着马的大侠,在路边捡到了这个被抛弃的孩子。只见他将孩子往身后一背,翻身上马驰骋如电。意象中似乎又过了很多年,原本的这个弃儿在大侠的养育和教导下,长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在心里,当故事以这种方式被讲述时,我们看到了另一种转化——跨原型转化。弃儿原型走向了英雄的命运,故事也从此进入了英雄原型的命运轨迹当中。就像我们常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无父无母的孩子历经坎坷磨难,最终成长为了故事里的大英雄。深圳心理咨询机构
再举一个例子:来访者在意象中看到了一个被丢弃在路边没人管的婴儿,正在撕心裂肺地哭着,看着就让人心疼。但接下来,来访者说到,任由这个孩子如何哭闹,意象中都不见有人来照料他。于是,哭得没有力气的婴儿,此时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中,眼看就要没有气息了……这时在一旁陪伴的咨询师介入了进来,她提示来访者说,看看能不能在想象中为这个弃婴的意象做点什么。于是,来访者说,“我在想象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孩子的妈妈……”而过了一段时间后,来访者有些沮丧地说,“找妈妈”的尝试并没有成功。这时,咨询师看到来访者似乎陷入了更为深沉的绝望当中。就在这时,咨询师开口对来访者说到:“让我们试着做一个想象,想象这时刚好有一位农妇经过了这里。”接着咨询师引导来访者,继续想象农妇将路边的弃婴抱了起来,又嚼了几口馍喂到了孩子的嘴里……深圳意象对话心理咨询师
在这之后,来访者回应说,她心里的这个弃儿的意象活了下来。连带着的则是她主观上在身体层面体验到的那种暖暖的感觉,以及在内心里感受到了踏实和满足。我们看到咨询师在这里做了一个介入,她引导来访者通过想象给意象中的弃儿找来了活下去的资源,也促使来访者的内心从被抛弃所带来的伤心、寒冷以及难以存活的绝望中,逐渐升起了对生命的希望。深圳意象对话心理师
这个过程里发生的,同样也是跨原型的转化。通过引入“大地母亲”原型的能量,令弃儿的命运轨迹在此发生了改变。在内心里,弃儿的故事中,走进了一位带来爱与希望的“好妈妈”。相应地,因着早年的“被抛弃”感而对关系缺少信任,在生活中屡遭挫败的来访者,在咨访关系中遇到了那位积极有爱,如同好妈妈一般的咨询师。
作者:史晋(水晶级意象对话心理师,意象对话创始人朱建军教授入室弟子),公众号:意象对话

扫一扫二维码关注心海湾